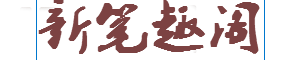66煤精石(1/2)
作品:《阴阳剪》&l; =&qu;&qu;&g;&l;/&g;&l; =&qu;250&qu;&g;&l;/&g;&l;&g;要不怎么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呢,我老家所在的村子,是方圆百十里,唯一一个会做陶器的地方。
我们那儿产黄土,山根儿底下,有不少地方都有十来米厚的黄土层。
那些黄土特别细致,晒干了之后,敲碎,再用水泡好,撒草木灰和泥,就可以做出来陶器胚子。
之后放到土窑里面烧制,出来就是黑陶了。
这门手艺是从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了,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位高人带到我们村儿的,就这么一辈儿一辈儿的传了下来。
而且特别奇怪的是,黄土不止我们村儿有。我们村子南北两边,相隔几里地就有其他村子,也有黄土,但是别的村子就是死活烧不出陶器来。
农村虽然搬家的少,但是通婚啥的,人口也有交。
几百年了,也不是没有烧陶器的手艺人,搬到那两个村子去,但是换了个地方,这陶器就是烧不成,要么裂开,要么烧不,一碰就烂。
只有在我们村,烧出来的陶器,黑黝黝带着暗光,拎起来用手指节一敲,那动静跟敲铜板一样,清脆悠长,半天都有回音。
这种黑陶盔子(饭盆),隔热,透气,煮的汤汤水水,冷粥热饭,三伏天放一天一宿都不带馊的,特别受迎。
穷的时候,我们村有不少人烧盔子、旋子(大的浅盘)之类的东西,骑着洋车子(自行车)到去换大米换粮食,养活了不少人。
这手艺现在也没断,不过烧的东西不再是盛饭的家伙事儿了,而是盆。
因为挨着旅游区,到搞绿化,盆的需求量大,我们村烧出来的陶器盆,又结实又透水透气,草草种到里边,成活率都比别的东西高,很受迎。
小时候最开心的记忆,就是跟着大伯,大半的去烧窑的人家串门儿,保准有窑口上烤出来的白薯吃,外表干,撕开之后香气直冒,糖浆得手都是。
要找这种煤石,看来得回一趟老家了。
叶子听我一说,也乐了。
虽然第二天是周一,学校的补习班还要上课,不过这时候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,只能请假。
第二天一大早,我和叶子带上东西,我买了几样点心,几白酒,一起回了村儿里。
在村儿里,虽然已经没有老萧家的人了,不过我妈那边儿,还有三个表舅。
三舅就是做盆的。
三蹦子进了村,我没有回家,直接让师傅开到了三舅家门口。
一敲门,三舅没在,不过妗子(舅妈)在呢。
三妗儿平时和我不太亲,我又背着一个克死家里人的臭名声,见到是我敲门,脸不太好。
不过等我把点心酒拎出来,脸立马缓和了些,开门让我们进去了。
我听了一下,三舅是去进煤了,晌午就可以回来。
我现在也学了,人世故明白了不少,知道三舅家还有俩表妹,都在上学,家里条件一般,麻溜的从兜里掏出两张一百块钱,说给表妹买点学习用品。
三妗儿嘴上说着不要不要,不过一张脸可是乐开了,当时的两百块钱,在农村还正经能顶点事儿,一般人家一个月生活费也就两三百块。
半推半就的收下钱之后,三妗儿就热的邀请我和叶子,晌午留下吃饭,我就等着她这句话呢,也没推辞,直接答应了。
三妗儿烙饼摊鸡蛋的功夫,三舅已经回来了,看见我在家,招呼了一声让我帮忙卸煤。
三舅这人高高,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,子直,心也善,跟我比较亲,小时候也没少照顾我。
当然了,跟我也不气,我这拎着点心酒上门做来了,直接把我拉过去,抡起铁锹卸煤。
叶子也没闲着,仨人一起干,没多大功夫煤就卸好了。
我擦擦汗,瞅着子里已经晾干的盆泥胚子,“三舅,今天烧窑吗?”
三舅拍了拍我肩膀,“是啊,后晌烧窑,你也别回去了,家里冷清,一会儿让你妗子给你收拾一下厢,晚上就住我这儿。晚上有烤白薯吃,你小时候最稀罕这东西了。”
我点点头,叶子一上听我说起烤白薯的美味,早就想吃了,更不用提。
村里的土窑,都是建在自家子里,个头不大,比住的还矮一截,所以外面看不到,这也是之前叶子来过我们村,但是不知道这里有土窑的原因。
土窑是用红砖和黄泥垒的,形状像个馒头,有一半是在地下,窑洞子前边有个坑,方便上下。
烧窑都是在后晌开始烧,把干透的泥胚在窑里边垒好,点火之后,用事先和好的黄泥和土砖,把窑洞封住。
再要添煤的时候,就要在窑顶上的烟囱口。
圆圆的窑顶上,倒扣着一个没有底的盆,既是烟囱,也是添煤、观察窑温的窗口。
一般要烧到后半,之后就彻底封窑,等到第二天早上,窑温降下来了,把窑洞开,里面的
本章未完,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 阴阳剪 最新章节66煤精石,网址:https://www.xbqg8.net/118/118130/67.html